文/申志(華夏陶瓷網首席記者)
旅途上的王宏偉
10月8日,下午,臺風過后的南莊陽光燦爛,御家瓷磚執行董事王宏偉在他的“御家文化吧”里,用他招牌式的笑臉迎接記者的到來。
一個月前,王宏偉和四名同伴一起自駕車經川藏線去了一趟西藏。作為陶瓷行業的新生代老板,出生于1980年的王宏偉,給人的印象是時尚、陽光,同時還有些“不誤正業”,因為當你要找他的時候,他總是人在旅途,你會懷疑他是不是成天旅游,而沒把功夫用在賣磚上。
我們的采訪就從一個月前的西藏之行開始。
旅行經驗:葡萄糖比紅景天更管用
對于這次旅行,王宏偉記憶猶新,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你把我又帶入了上個月的情景中去”……
9月3日那天,王宏偉的西藏自駕之行從四川成都開始。一行五人,都是熱愛攝影的陶瓷從業者,他們租了兩輛越野車,還請了一名地導。
從成都出發,第一站是到四姑娘山,然后一行人去了雅安的甲居藏寨。王宏偉告訴記者,當地人屬丹巴藏族。一路風光美如畫,且看且走,他們經過了八美、新都橋,之后轉道去稻城、亞丁、芒康、洛隆。王宏偉回憶,他們在洛隆從國道318線轉走國道303線,但目的地沒變,仍然是拉薩。在這之后,一行人還去了納木措,之后是到拉薩,到拉薩后又去了一趟羊卓雍措,最后從拉薩飛回廣州。
王宏偉等人的西藏自駕車之行,大致行程就是這樣的。說起來簡單,但途中卻有很多難忘的人和事。譬如,王宏偉是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第一天晚上到四姑娘山時就遭遇了高原反應,他說,“頭疼了一陣子,到了凌晨兩三點睡熟以后就沒感覺了……”
雖然沒有明顯的高原反應,但畢竟高原氧氣不足,如果快走就會氣喘。這一路,從海拔四千米到海拔六千米,王宏偉半夜會有睡覺時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但是他不緊張,因為在“上山”之前他已經做了充足的準備。
說到去西藏的準備,王宏偉說,九月在西藏已是秋天,要帶外套,還要帶雨衣,因為高原的天氣反復無常,“高原的天,娃娃的臉,說變就變”。除了必要的裝備,還要帶藥品,以紅景天、葡萄糖(注射用的那種)為主。
其中紅景天是每個去青藏高原的人都被告之要提前服用的抗高原反應的良藥,王宏偉也不例外,“上山”之前,他提前一個星期吃紅景天。但是他感覺紅景天并沒有太大作用,套用當下時髦的網絡語,那叫“然并卵”。王宏偉告訴記者,“真正有高原反應,準備點葡萄糖,當你感覺呼吸不順暢,葡萄糖里注入一些溫開水,喝點這個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喝葡萄糖水遏制高原反應,這是曾有過藏區生活經驗的記者第一次聽說,那么從未上過青藏高原的王宏偉是怎樣得到這個經驗的呢?他說,是地導告訴他的。接受了地導的建議后,王宏偉等人在成都買了不少葡萄糖,有人還覺得買多了,而后途中的事實告訴大家,葡萄糖非常管用,所有那些葡萄糖最后全部都喝完了,一點都沒浪費。
在青藏高原放飛心情
壯麗的風光
藍色的高原湖泊
藏區印象:人因信仰而偉大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去西藏旅游還沒形成風氣時,在去西藏的旅行者中就有個說法,“身體下地獄,眼睛上天堂,靈魂回故鄉”。
王宏偉此次去西藏,感觸很多。他說自己長這么大,從沒見過這么漂亮的云彩,從沒見過這么藍的天。看著藏區的藍天白云,王宏偉感覺一伸手就可以摸到白云。說到這里,他引用了一句在旅行者中廣為傳誦的“語錄”,“西藏是離天最近的地方”。
作為一個大齡文藝青年,王宏偉認為藏區的天之所以那么藍,云之所以那么白,就是因為沒什么工業污染。而這話如果放在早幾年前的南莊來說,那會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旅途上的壯麗風光是一方面,更讓王宏偉感動的則是旅途上遇到的人——藏民。
在王宏偉眼里,藏民臉上充滿了樸實、樸素的表情,尤其是那些磕長頭的朝圣者,讓他非常震撼。他說,“試想一個尋常人,不要說一步三叩首,步行去拉薩都難以做到,但人家是磕著長頭到拉薩。”
到達拉薩以后,王宏偉等人去了大昭寺和布達拉宮,它們的外圍全部是佛教徒在朝圣,場面很壯觀。在大昭寺,導游問他們看到柱子沒有?他們說看到了。那柱子里面鑲滿了牙齒。導游告訴他們,這些牙齒的來源,是死在半路的朝圣者——同伴把他們的牙齒取下來,帶到拉薩,鑲到大昭寺前的柱子里,象征他們也完成了這次朝圣之旅,——靈魂隨牙齒一起到達了拉薩。
這件事尤其讓王宏偉震撼。沿途他看到的藏族老人,不管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每個人都捻著一串佛珠,他們一邊走,一邊念念有詞(不是在唱歌,應該是在念經,這就是信仰——這是王宏偉的判斷)。
對于信仰這件事,王宏偉曾經和一個藏民交流過,藏民告訴他,到拉薩朝圣是完成一生中神圣的使命。王宏偉告訴記者:人因信仰而偉大。
走過獅子雕像的小喇嘛
王宏偉從內心里接受藏傳佛教
雪域愛情:倉央嘉措和文成公主都讓我感動
佛教講因果,佛教徒講來生,對于藏傳佛教的信徒來說,到拉薩朝圣就是求來生。但是,偏偏藏傳佛教徒中卻有不求來生只求今生的人,并且這人在藏傳佛教中地位還相當高,他就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王宏偉骨子里非常喜歡倉央嘉措這個人。在那格拉,他特意拍了倉央嘉措留下的一幅詞(碑文),“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遇”。
倉央嘉措與瑪吉阿米的故事廣為流傳,比如著名歌唱家譚晶曾唱過一首《在那東山頂上》,歌詞寫的就是倉央嘉措與瑪吉阿米的故事。而與王宏偉相熟的佛山詩人包悅,更是寫出了一部長達數千行的長詩《瑪吉阿米》。王宏偉眼里的倉央嘉措就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是一個情種,“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如果他不是活佛,相信他會有更多的著作,有更多關于他的傳說。”
還有一件讓王宏偉難忘的事,在拉薩河邊,一行人觀看文成公主的史詩劇表演。那部史詩劇呈現的一千三百年前文成公主和松贊干普的傳說,幾千人參演的大型史詩劇,場面很壯觀,由譚晶演唱的歌詞,更是深深地打動了王宏偉,“走不到的地方叫遠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天下沒有遠方,人間都是故鄉”。聽到這段的時候,王宏偉流淚了,因為這段歌詞文字的美深深地打動了他。他說,“我們何嘗不是另一個文成公主,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創造新的世界?”
王宏偉老家在安徽靈璧,該地是楚漢相爭的古戰場,流傳至今的成語“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以及項羽的“垓下歌”皆出于該地。據了解,靈璧還是唐代進士鐘馗的故里。對故鄉情深意切的王宏偉,曾用一首古體詩詠嘆過自己的思鄉情,“為謀生計走四方,思鄉愁酒經年嘗。夢里家鄉幾回見,鄉音鄉土最思量”。
旅途風光是一面鏡子可以折射人的內心
勞逸結合:在旅途當中思考戰略
王宏偉喜歡旅游,在行業內是出了名的你,要找他的時候,他常常“在路上”。
王宏偉細數了一下今年的出行清單:
三月去江西婺源;
五月去福建霞浦;
七月去蘇杭;
八月去湖南的小東江;
九月去西藏……
去蘇杭是為了追尋煙雨江南的感受。而霞浦,搞攝影的人都知道,是中國攝影基地,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灘涂。
如果把這份出行清單再拉長一點,那么可以看到去年王宏偉也去了好幾個地方,比如他曾自駕車去新疆,到喀納斯、克拉瑪依、魔鬼城、可可托里轉了一圈,還去了一趟歐洲——法國、瑞士、意大利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陶瓷行業的從業者都像蜜蜂一樣忙碌,佛山的陶瓷企業甚少有周末雙休的,一個月休四天的算好的,有的企業一個月只能休兩天。像王宏偉這樣有大把時間用來旅游的,在佛山的陶瓷行業從業者中顯得相當“另類”。
王宏偉有自己的解釋,他說自己有一顆文藝的心,有浪漫主義情調。處女座的王宏偉,他對旅游的詮釋,或者說對工作和生活結合的理解是:人未必每天工作就能做好工作。
很多人問過他:你這么多次旅行,不影響工作嗎?
他的回答是:在我看來,放下自己才能做好自己。
王宏偉接著向記者解釋,中國有句成語叫“勞逸結合”,當他覺得自己沒有狀態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外界其他的渠道找方法。而他的方法其實就是在旅行當中去尋找自己,在旅途當中思考工作。
王宏偉說,“我一邊在旅行,更多的卻是在思考。”他把自己的旅行比作“身在曹營心在漢”。那么“在漢”是要考慮哪些問題呢?他考慮的是旅行回來之后要解決的那些問題。王宏偉鄭重其事地告訴記者,御家瓷磚的每一次改革——包括人事改革、產品改革、公司發展戰略的制定,都是他在路上形成的思路。
其實,如果回溯一下王宏偉的職業生涯,就會發現他并不是一個喜歡無所事事的人,他其實是一個相當勤快的人。
2005年王宏偉從東莞長安來到佛山,在駿仕做業務員,僅用了一年時間,就因為業績突出被提拔為副總。而后,他在廣西新中陶任品牌營銷總經理,在升華企業的酷高品牌任營銷總經理,并于2013年年底與朋友合伙創辦御家瓷磚。
在“把青春熱血灑在了佛山這片陶土上”(自謔之語)的王宏偉看來,做銷售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用業績來說話。“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惰”,他認為這就是做好業務的標準——業務人員必須得勤快,還要學會用腦子去思考。他說:“人一懶惰,或者抱著僥幸心理,肯定做不好。”
結合當前的市場,王宏偉認為很多時候大家都在哀怨,哀怨市場如何的不景氣,哀怨員工如何的難管理,但在他看來,哀怨不如改變。他說,“人挪活,樹挪死,換一種思路,或許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也許,喜歡“在路上”,就是換一種思路的王宏偉的工作方式。
同一個景點不同的時段拍出的效果截然不同
“不誤正業”:藝術是無用之大用
王宏偉的辦公室,原本設在御家瓷磚總部展廳的二樓,里面擺滿了書畫、陶藝、茶具之類的東西,非常有文藝氣息,時常高朋滿座。現在,他把自己的辦公室搬到了一樓大堂旁邊,那是個有180平方米的空間,層高6米,里面有酒吧、圖書閱覽區、書畫桌、投影儀,酒吧里有洋酒,紅酒和咖啡即將“進駐”,被他命名為“御家文化吧”,來的人就更多了。今年10月1日,王宏偉在這里宴請朋友,并美其名曰“御宴”。
之所以把自己的辦公室搞成這么一個綜合性藝術吧,王宏偉告訴記者,那時因為好的環境才能產生好的思維。空間寬闊,外面還有鮮花,喝著茶,聽著古典音樂,他反問記者,“是不是感覺很好?”
王宏偉對自己的評價是:我覺得自己是這樣一個人,外剛內柔,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看似粗獷的外表之下,有一顆細膩的心。
他喜歡文學,喜歡與藝術相關的東西,很多不了解他的人會有疑問:你會喜歡看書?這話真是傷自尊,他向記者感慨:以貌取人是不可取的事情。
崇尚自由的王宏偉,收藏書畫、陶藝,還寫詩、攝影,以及養魚種花。他愛跟美女聊天,喜歡香道。在陶瓷行業,王宏偉的女性朋友很多,在這一點上,他儼然也具有倉央嘉措的氣質。
對于設計(平面)王宏偉興趣也很濃,御家瓷磚幾乎所有圖冊的設計,包括公司LOGO的設計,都有王宏偉的痕跡——有他對于美的追求,以及對于空間的詮釋,和對于產品的理解。
御家瓷磚有一本圖冊,里面用“煙雨江南”作為文化背景,而這“煙雨江南”就是王宏偉本人去蘇杭旅游找回來的感覺。
在王宏偉看來,藝術是為生活而服務的,藝術源于生活,最終又服務于生活。藝術是無用之大用,所以王宏偉要給自己的愛好正名,他說自己的“不務正業”應該換一個字,叫“不誤正業”。
“我們這么努力地工作是為什么?生活。那你活得這么累的話還叫生活嗎?”對于工作與生活的關系,王宏偉的看法與陶瓷行業的絕大多數人不一樣,他說,“我們這么努力、這么辛苦地去賺錢,就是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好。可是你這么辛苦,錢賺到了,反而不去生活了,健康沒有了,親情也沒有了……”
特別強調生活的王宏偉,對“生活”本身也進行了“辯護”,“這不是說大家都不要努力去工作了,我們的工作是為了好好地生活,那么好好地生活是不是為了更好地工作?”在他看來,歐洲人和美國人都特別強調生活,假期很多,但為什么創造力還那么強?他推導的結果就是:工作與生活是可以結合的。
對于中國陶瓷行業的同行時下熱衷的一件事情——去博洛尼亞觀展,王宏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訴記者,很多人都去博洛尼亞觀展,他問過一些人此行有沒有收獲,對方的回答是沒什么看頭。王宏偉直言不諱地批評,“我們去博洛尼亞學習,學什么?要學歐洲產品的工匠精神,要學習人家產品的設計空間感,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去博洛尼亞是白去了。”
至寶山而空手歸,那些人也許是不懂得藝術是無用之大用的精神,也許是不懂得工作要與生活結合的真諦。
迷你酒吧
健身單車
石磨茶座
書畫桌下的古琴凳
創業緣由:實現自己的老板夢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1963年做過一次非常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王宏偉也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自己當老板。
如果說創建品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老板夢,那么品牌創建之后,王宏偉感受更深的則是自己肩負著一種責任和使命。具體來說,手下有幾十號員工,那就代表著幾十個家庭,這幾十個家庭生活質量的好壞都是跟他息息相關的。還有諸多代理商,選擇御家瓷磚,建專賣店,在各方面投入,也是因為與他王宏偉相關。王宏偉很認真地說,“先不要講大的社會的公德心,首先我們必須具備企業的公德心,就是責任。這么多員工的家庭,他們要買車買房吃飯,要靠你這個老板去發工資呀。代理商一年能賺多少錢,也要靠你這個企業的良性運行和服務。”
對于御家這個品牌的定位,王宏偉坦言有個人在美學上的偏好。
中國有句古話叫“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是什么樣的人,就注定你帶什么樣的兵。王宏偉對自己的團隊和董事會都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他希望把御家做成“按照單品類,以產品為核心競爭力,真正實現產品空間應用一體化的品牌”。他告訴記者,自己在四十歲之前的目標是,“不管外面的風有多大,雨有多狂,我必須讓企業在艱難的環境下良性運轉”,只有這樣他才覺得自己會不辜負董事會以及代理商對他的期望。
那么,四十歲以后呢?王宏偉表示,到那時他可能會玩一些真正屬于自己愛好的事情,比如學畫畫、陶藝之類,并在這些領域有所發展。
王宏偉喜歡文學,每天在微信里“胡言亂語”(自嘲語),而這個愛好可以追溯到他的父親。他告訴記者,他的父親是一位教師,教齡有三十多年了,現在家寫書(寫小說)。談起父親,王宏偉很自豪,他說,“他的詩歌也寫得很好。”
王宏偉一向以家學自豪,所以父親走過的路,他也要去嘗試。他說,“四十歲之前,我是為了生存;四十歲以后,我必須要為了自己的生活……人生短暫,我不能等到人不在的那一天才想想自己這一輩子——什么都做了,但什么都沒做好,留下遺憾。”
這樣看來,未來王宏偉還會干些別人眼中的“不務正業”的事兒,一如他常年“在路上”。
霞浦風光
江南民居
鄉野情趣
(旅游照片均為受訪者本人提供)



















 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頭條焦點
頭條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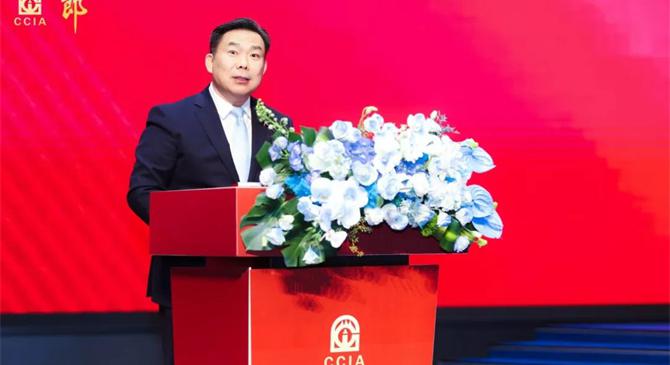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