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訪者:李華東(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
采訪者:申志(華夏陶瓷網首席記者)
來自北京工業大學的學者李華東,身材瘦弱,講話聲音很輕,且為人謙和,即使是演講現場被聽眾沖撞他也不急不惱。但是,外表柔弱的他內心卻很強大。李華東這些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作。他是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專家委員會工作組成員,不但在學術研究上走在前沿,還身體力行搞田野調查、推動保護工作的落實,成為這一領域的知名學者。而這一切,來源于他內心對中國建筑歷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從他的學術背景,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的那一批優秀學人。而中華民族的文人傳統,也就是靠李華東這樣的人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的。
外表柔弱內心強大的學者李華東
背景:個人主要學術方向是文化遺產保護和鄉村遺產保護
申:請先介紹一下您的成長背景和學術背景——您本科是在清華大學讀的,研究生呢?
李:我在清華學的建筑歷史,尤其對咱們中國的建筑歷史特別感興趣。本科畢業以后呢,我覺得(要關注)東亞的系列文化圈——中國的建筑怎么傳到朝鮮半島,又怎么影響到日本的?當時自己有一個粗淺的規劃,就是到朝鮮半島繼續學建筑歷史,讀碩士,然后到日本去讀博士,這樣東亞三個主要國家的建筑歷史都基本掌握了。我的研究生是在韓國讀的,但研究生畢業的時候,趕上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日本方面不提供獎學金,而我不愿意像傳說中的勵志小說寫的那樣,洗十個小時盤子,然后又趕到學校學習,那樣我做不到。干脆又回到清華讀博士。
其實我和咱們這個室內設計是蠻有淵源的,原來我在中國建筑裝飾協會的雜志《中國建筑裝飾裝修》做了兩年執行主編,大概是2003年至2005年。所以我對室內設計界也有關聯,這次來深圳(參加設計師活動),(感覺)特別親切。
申:您在清華大學學建筑歷史,相信與梁思成先生也有傳承。
李:如果不是說大話的話,我算是梁思成先生的徒孫吧,因為我本科的導師、博士生的導師是梁思成的弟子。
申:從您接受的公開采訪看得出來,這種傳承有些影子,包括對古建筑著迷的勁兒。當年梁思成先生與林徽因先生特別喜歡去考察古建筑。
李:我們國家從2012年開始投入很大的精力,包括人力、技術力量、行政力量、資金(主要是中央財政),做中國傳統村落的保護發展工作。到目前為止是七個部委(住建部、文化部、農業部、國土資源部、國家文物局、國家旅游局、財政部)來做這個工作,為此成立了一個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是一個智囊機構,為了讓專家委員會開展工作,又成立了一個工作組。
申:您在哪所大學任教?
李:北京工業大學建規學院,副教授,教學方向是根據上級領導安排,教建筑設計也可以,教風景園林也可以。當然我自己主要研究的領域,在2012年以前是文化遺產保護——就是保護一些文化單位,從學術研究、規劃到保護、修繕;2012年以后,有幸進入國家傳統村落保護的工作中,一直干到現在。我主要的方向就在文化遺產保護和鄉村遺產保護這方面。
拗口的題目下,是李華東濃厚的人文情懷
一張圖片揭示的鄉村文化悖論
現狀:傳統村落保護有成績問題也不少
申:那您覺得,在您的專業方向,目前我國的現狀是怎樣?請您簡單介紹一下。
李:從個人觀點來說,關于傳統村落保護,第一是得到了很大的重視。到本屆政府執政,文化遺產包括鄉村文化遺產保護,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鄉愁”,到各級政府,還有社會各界,包括咱們的文化設計界、室內設計界,重視程度是提高了,這是大背景。
第二點,取得了很大成績。單就我最近從事的傳統村落保護這個事來說,我們國家大規模地普查、摸底,這在世界上也是很大的一個行動——通過全國的力量調查了兩萬多個傳統村落,分批公布了各級的保護名錄,國家級的傳統村落(個別先進省份,比如廣東,也公布了省級保護村落)前后有三批,國家級的傳統村落有2225個,目前正在評國家級的第四批,(我們)不斷地擴大保護的名錄和范圍。國家也有實實在在的支持,比如中央財政前段時間安排了114億元專項資金,支持傳統村落保護工作。在人才隊伍、機制建設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三點,問題也不少,比如政策和機制的問題——資金怎么下發、使用,人才怎么培養?除了學校里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村落里的傳統工匠,他們是主力,木匠、石匠……在農村很多時候是這樣的情況,因為這個手藝不賺錢,老人去世以后就丟掉了,我們的房子不知道怎么修,我們沒有石匠、木匠、泥瓦匠,城里的施工隊只知道搞現代建筑,砸鋼筋,澆水泥,農村很多東西就是這樣消亡了。資金,國家很努力,各級政府也有投入,但就全國而言還是短缺,那么多傳統的老房子要修,是個天文數字。傳統工匠的短缺,還有自然的威脅——火災、洪水,諸如此類的,看新聞常有一場火燒掉一個寨子。
李華東列舉了傳統村落保護的部分成功案例
富足的精神生活是鄉村建設中必不可缺的內容
問題:現在的保護沒有轉化成一種自發的行為
申:您覺得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什么?
李:我個人感覺最嚴重的問題還是人的思想觀念問題,現在的保護沒有轉化成一種自發的行為,對某些領導干部來說只是國家有要求才做,而且不同的領導干部看法不一樣,說得通俗一點,坐在什么板凳上想什么問題,村鎮干部和縣委書記想的不一樣,縣委書記和省里的領導想的不一樣,省里領導想的……應該上下都保持高度一致,但實際操作起來還是有一定的差別。
農村的工作和城市不一樣,城市條塊分割很厲害,農村則是一個整體,一個系統。有社會心理的問題,就必定有政策的問題,然后就會有實實在在的技術措施的問題,有資金投入的問題,還有產業的問題。單從我們這個行當來說,涉及人員的觀念問題,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理解農村到底是什么。我們按照城市規劃學、城市建筑學培養出來的規劃學、建筑師,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在用工業時代的觀點、西方的思維(因為我們這套體系實際上是西方的)、城市的觀點來看待農村。從這樣的認知基礎來看待農村,就導致農村里相當一部分可以說被破壞了。
破壞大致可以分三種:一種是自然的衰敗。有的村落遠離交通線,地質不安全,生態環境惡劣,撤村并點,或者說日曬雨淋沒錢修復,就自然衰敗掉了。第二種,是建設性的破壞,大拆大建,拆舊建新,為了發展土地財政,建設性破壞的危害性很大。通過努力,建設性的破壞現在得到了遏制。最隱性的一種破壞,大家不但不注意,甚至還使勁鼓吹,就是保護性破壞,拿了錢,比如中央給了資金,您剛才說的思想觀念不正確,(導致)好心辦壞事。
困難:鄉村建設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新問題
申:修舊如新,就是這樣干的。
李:這種現象在今天反而變成突出的矛盾。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到處去探討,去宣講,不停地辯論,分析。
嚴格說起來,鄉村建設這一塊,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它是新問題,雖然說中國幾千年一直是個農業社會,但這個時代我們對農村的認識反而模糊不清了。認知基礎不清楚,行動的途徑和方向不清楚,那具體的路徑和措施就更有問題,所以這是重新從零開始的一個階段。不僅是從學術上重新開始研究,重新開始認識,在行政上既有的模式也要探討。實際的工作中很具體很微觀的層面,怎么做規劃,怎么做設計,我們現在都有一個共識——從零開始,實事求是,以問題為導向,拋開過去的條條框框,真真正正把腳站在土地上,然后以我們的村民為主要服務對象,解決他們存在的實實在在的問題,以這為出發點來探討、研究規劃的工作該怎么做。
所以,總結一下:全社會很重視,取得了很大成績,還有很多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觀念問題,我們目前相當一部分人還是在以工業時代的觀點、西方的觀點、城市的觀點來看待鄉村。
譬如說新農村建設,成績很大,造成的問題也很多,最關鍵的還是咱們并不了解農村,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大別山農村為了給農民解決人豬分離的問題,在村邊建了“托豬所”,也就是集體養殖,豬還是你的,但是集中飼養。這就是典型的以城市的觀點看待農村。豬和人住在一起,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態循環體系,人吃剩的飯菜不浪費,倒到豬圈里,豬吃,豬的糞便可以為蔬菜施肥。過去的農村沒聽說什么垃圾問題,現在的農村垃圾反而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建那個“托豬所”,村民不愿意,政府白花了錢,誰會端著潲水走那么遠?哪怕再近,騎摩托車也要走四五分鐘。這就是您剛才說的,方向錯了。我們要研究的不是讓豬和人分離,而是要研究豬和人在一起的優點,同時避免蚊蠅亂飛、臭氣彌漫這種缺點,找到辦法,這才是解決鄉村問題正確的路子。而不是拋棄它的優點,發揚缺點。
方向:農村不是要拯救的對象,要拯救的是城市
李: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對農村認知不清楚,認知不清楚,每個問題都可能發展成一篇大文章。目前的心態還是居高監下去看待鄉村。甚至包括“送文化下鄉”,某些方面是對的,豐富鄉村的文化生活,但是在某些具體的層面上是有問題的,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非常有文化,都是當年中原的名門望族一點一點遷過來的。最正宗的漢人就是客家人。
申:他們才是真正的貴族。
李:我們不但沒去挖掘我們的優秀文化,反而先天地認為這是落后的文化,要干掉的文化。然后就說什么文化下鄉,送什么“鳳凰傳奇”,這是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我們要擺正心態,農村不是我們要拯救的對象,反而要拯救的是城市,城市病很嚴重。比如在城里,老頭老太倒地沒人敢扶,所以某保險公司出了個“扶老人險”,但這個賠償的不是你賠老人的錢,而是賠你的訴訟費。就是你可以用這個錢去請律師。一個社會變成這樣子,我們樓再高,車再多,燈再亮,物質生活再豐富……
申:您剛才講的這個例子我深有感觸,我也是做公益的人,在城市里面,碰到有人跌倒,我真不敢扶,手都伸出去了。
李:那找個人站在旁邊錄像。
申:好在那情況不嚴重,人家能起來。像我這樣的人都不敢去扶,這種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江蘇南京那個判例(“以常理推斷”案例),影響真的很壞。
李:管中窺豹,小中見大。
觀點:中華民族要崛起,需要文化凝聚力
李:經過建國以來這么長時間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有一些問題,經濟結構的問題,生態環境的問題,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一些現象,真正的原因就是文化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很多跟鄉村相關的,比如開始強調鄉規民約,強調鄉賢,強調傳統的道德——忠、孝、禮、義、恥。比如我們的生態環境污染,好像是產業發展的問題,歸根到底是道德的問題,一個有良心的人,有責任的人,有傳統道德觀念的人,怎么狠得下心把重金屬注到地下,排到水里去?就為了一點點錢。排到水里去還好了,地表水經過認真的治理,三年五載,十多年,還能治好,惡劣的是打地下深井,免得被查,污染水源,上萬年也解決不了。這不是技術問題,是道德問題,所以我們社會發展到現在,遇到很大的危機,遇到很大的瓶頸,最大的障礙就是文化問題。我們社會為此付出很高昂的成本,大家錢是有了,幸福感提升沒有不敢說。
如果再扯大一點,對整個世界來說,中國人的文化面貌是模糊的,就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到底是什么人,所以他就防著你。你撒錢,減免窮國的債務,用咱們老百姓的話說換來的是“酒肉朋友”,今天有酒肉就跟著你,明天沒錢他就鬧著要去跟那個島去建交。無賴國家不就玩這個嗎?他從內心里不認同你。但如果通過精神和文化認同結交的朋友,那就不一樣。對外,人家不知道我們是什么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整個民族的文化認同感越來越薄。連戰為什么到大陸來,這些老一代的還堅持“一個中國”,就是文化認同,他說“我是中國人”。可是如果你不保護鄉村遺產,比如很多海外華僑的祖墳都被刨掉了,他回來祭祖沒有祠堂沒有祖墳,他回來干什么?
申:當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故鄉就是有祖墳的地方》。
李:中華民族要崛起,全世界華人要有凝聚力,不是說你有錢就行,它是文化凝聚力,不是錢的凝聚力。民國時期我們多窮?抗戰,那么多的華僑給錢出力,還死了很多人,因為他心里還有祖國在。我們社會有很多問題,最嚴重的就是文化問題,洋務運動沒有沖擊,只是在技術層面弄了些洋槍洋炮,五四,土改,文革,再加上改革開放帶來的沖擊,我們的傳統文化已經被沖擊得七七八八了。
申:過去的價值觀已經被破壞掉了。
李:我們搞文化遺產保護,不是普通人理解的那樣,修幾個破廟,那些東西本身并不重要,但背后承載的東西重要,那是我們文化的根源。對一個人而言可以沒有祖宗,我就不要祖宗,我就石頭蹦出來的,我就做毒食品,做假冒偽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行,我們必須知道從哪來,我是誰,向哪去。
申:感謝您今天接受我們的采訪,非常感謝!
李:也謝謝您,以后我們多交流。
鄉村文化建設關聯著中華文化的復興
個人簡介:
李華東,男,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學報》特邀編輯,《中國建筑文化遺產》雜志編委,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專家委員會工作組成員。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系建筑學學士(1996)、韓國蔚山大學建筑學院建筑學碩士(1998)、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歷史與文物建筑保護研究所博士(2006)。
研究方向主要為文化遺產保護、建筑歷史與理論。先后參加了北京市傳統建筑病害現狀調研評估(國家文物局課題)、明清官式營造技藝地方化背景下的五臺山漢藏佛寺彩畫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內蒙古長城雞鹿塞保護規劃(內蒙古文物信息中心委托項目)、中國古代建筑與營造科學價值挖掘研究(國家文物局科研項目)、中國古建筑精細測繪(國家文物局項目)、國家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護規劃規范編制(住建部課題)等科研項目,并先后主持編制了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總體規劃。
發表有《西藏寺院壁畫藝術》、《高麗時代木構建筑和<營造法式>的比較》、《中、日、韓三國的木塔》、《杭州西湖雷峰新塔》等論文,著有《世界著名城市建筑導讀——北京》、《西方建筑》、《朝鮮半島古代建筑文化》、《高科術生態建筑》、《超越東西方的設計》等專著。
觸目驚心的現實讓人動容








 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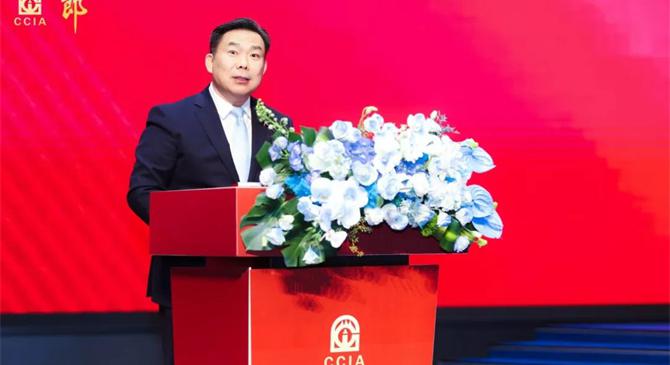



 頭條焦點
頭條焦點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