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訪者:盧敦穆(原佛陶集團副總經理)
采訪者:劉小明(華夏陶瓷網總編)
整理者:申志(華夏陶瓷網首席記者)
身材瘦高的盧敦穆,是由佛陶集團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型管理人員,他親眼見證了佛山陶瓷的四個發展階段,并在利華廠全線引進的關鍵時期擔綱安裝、調試總指揮,成功打破用水煤氣燒有顏色的彩釉磚這一世界性難題,并且成功消化吸收國外建陶先進生產設備,為我為陶瓷行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盧敦穆向記者一行繪圖說明設備的運作原理

盧敦穆的手繪圖
石灣陶瓷產業的四個階段
劉: 請談談你的經歷,包括做陶瓷的經歷。你是哪一年進入佛陶的?
盧: 我是中山縣小欖鎮人,在家鄉念書,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959年到廣州華南工學院念書(5年),1964年畢業分配到石灣耐酸陶瓷廠,一干干到退休,干了幾十年陶瓷。
我來石灣以后,經歷了產業發展的四個階段:我來之前石灣正好是“三煲”時期,粥煲、飯煲、茶煲,這是石灣的代表產品;發展的第二階段就是化工陶瓷,就是專門做耐酸磚、耐酸管、耐酸瓶、琉璃產品;第三階段就是建陶產業了,就是周總(指周棣華)所說的引進設備建陶產業發展這個時期了;最后一個階段就是多元化的綜合體時期。為什么說多元化的綜合體呢?我們石灣不單生產陶瓷,還有其他配件統統發展起來了,包括釉料、原料、耐火材料、輥棒、機械、電器,構成一個綜合體,所以我們石灣可以足不出門,生產陶瓷的所有設備自己能解決,其他產區沒有,這一點是我們作為石灣人、佛山人的驕傲。中國的其他產區,包括最有名的唐山、四川、醴陵,都沒有我們佛山這個特點,有些東西還是要到我們這里來買。
劉: 你這四個階段的時間是怎么劃分的?
盧: “三煲”,五幾年差不多就開始了,解放初期這一段時間,我們石灣還是在生產三煲的;化工陶瓷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開始生產;1978年后到1988年,設備引進的時候,是我們建陶發展最快的時候,是高峰;1996年以后,我們石灣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構成。這四個階段代表我們石灣陶瓷發展的節點。
劉: 為什么說是1996年以后是多元化時代?
盧: 因為1996年以后我們引進基本結束了。1996年以后引進的不多,有也不是整線了,都是單機買的。我們利華廠當時是全線引進。為什么說是全線引進?我們那時候連螺絲釘都是從意大利買回來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受的壓力很大的,特別是周總,他是組長,我是跟著他學東西。引進回來以后,我就是生產線的總指揮,安裝,投產,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引進設備最大的風險是能否拿出產品
劉: 你是總指揮?
盧: 周總他是引進的組長,我和趙敏昌是幫他搞其他東西的,引進來以后,就由我去負責安裝,他把其他時間用于其他工廠的引進,建國廠、建華廠、石灣瓷廠、工業廠……他是管面的,我是管點的。在耐酸廠重點搞了一年時間,把設備引進來,安裝,到投產。
劉: 安裝了多久?
盧: 差不多一年時間。
劉: 安裝小組是哪幾個人?
盧: 我是總負責,霍達忠、陳中治、譚錦棠(盧:那個時候他是副書記)、黃福林,還有副廠長韓炳泉。我回來以后就當副廠長了。我是1983年當副廠長的,我和周總去考察時還是科長。我1964年畢業以后到耐酸廠,起初是職員,然后是設備科副科長、科長,1983年當副廠長,1984年當廠長,1986年兼黨委書記,1990年我到陶瓷公司當副總經理,在公司負責生產、科技、技術。
引進最大的風險是有沒有把握把產品拿出來。我們上石灣鎮匯報的時候,鎮委書記跟周總說:你有沒有把握?有把握你就要成功,沒有把握你要下臺。周總交待我:老盧你去耐酸廠把設備安裝好,生產出來,這是你的義務,你要干好,你要干得不好就不行。
劉: 安裝過程中出過什么問題?
盧: 出現問題很多。
劉: 是在老外的指導下安裝還是自己安裝?
盧: 我們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我是組長,下面還有骨干。我們要請示上級,爭取他們的支持。我們請示了佛山市后來的經委、科委,去招人,后來佛山的市委書記、市長鐘光超,是我那時要求他到利華廠去廠幫我們安裝機器的。他是負責電器自動化的,他那時在佛山市科委,是個科員。他是負責電器自動化的安裝,黃福林、霍達忠是和張銘昌一起搞設備安裝。
劉: 鐘光超他是學什么的?
盧: 學自動化的。所以我們那個時候邀請他到我們廠搞自動化安裝,因為引進設備牽涉到很多自動化設備和電器。
劉: 他在廠里干了多久?
盧: 他在我們廠干了一年時間,是我們從科委借調來的,等到生產設備投產了,他又到建國廠去了。
第三個風險是你的指標能否滿足生產需要。周總提到“三包”——包產量、包質量、包能耗,那三個指標最大關鍵就是我們的煤氣發生爐,我們是從佛山農藥廠把煤氣發生爐拿回來的。后來生產出來了。有一天霍達忠到我家找我,那天休息,利華廠剛好生產了,煤氣出來的水分多,灰塵多,硫氣多,把那個噴嘴都堵塞了,沒有煤氣出來。沒有煤氣出來怎么燒產品呢?霍達忠和張銘昌到我家來找我,生產車間找他們,他們就來找我了。我們馬上開車到工廠去指揮。后來把那個噴嘴拔出來,因為噴嘴那個孔很小,干脆把它拿出來,再進行燃燒,就解決了問題。因為煤氣不堵塞就暢通,一暢通溫度就提高了,產品就出來了,就這么簡單。水分霧化,灰塵堵住了噴嘴,復雜的問題簡單處理。
解剖設備,把外國專家調虎離山
盧: 我們安裝的時候有一個插曲,設備進來后,我們不能動,打好包裝的,用絲封起來,專家來了再把絲解開,讓我們把設備一個一個裝起來。有些東西我們想了解的時候,他不給看。你想看它螺絲結構是怎么樣的也不給看。
劉: 他不是來教你們的嗎?
盧: 教,但是不給看。這個放在這里,那個放在那里,他就指揮。你想打開看,不給看。那你專家走了我們就可以看了嘛。這不關我專家的事,這是公司的事。他們是這么認為的。后來我們成立了一個吸收消化小組,張銘昌、霍達忠是組長,我們組織這些人,要把里面的設備、結構研究透。他有3個專家,有時晚上也在那里,3個專家每人8小時,看住設備。
劉: 是在燒之前?
盧: 在設備進來時,先要拆開再安裝嘛。后來我們廠想了一個辦法,請了一個女翻譯,帶他們三個專家休息兩天。最初他們還不肯:我在這里安裝設備,我要管好這些設備,怕工人弄臟了弄壞了,我怎么對公司負責?后來我跟他們說:我們西樵那是個風景區,你們休息的時候我們也不干活的,我們會把車間封起來的。女翻譯就帶著他們去玩,他們一走,我們就把設備拆開來看。消化吸收小組有13個人。
劉: 兩天時間?
盧: 一個星期兩天,反正一到周六、周日他們就去玩,我們就在車間拆,他回來之前就把蓋封起來。為什么佛陶集團能夠多元化,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把別人的設備統統研究透了。所以我們最偉大的地方就在這里,我們不是為了引進,而是為了吸收它的技術,解剖它。所以才有今天陶瓷行業的蓬勃發展。
蕭華是幫我們搞設備的個體戶
劉: 你那個消化吸收小組后來有沒有自己當老板的?
盧: 有啊,蒙娜麗莎的蕭華以前就是搞那個設備消化小組的,他不是正式成員,但和他有掛鉤的關系。
劉: 蕭華后來是搞窯爐吧?
盧: 最初不是搞窯爐,是搞噴霧干燥器,他是靠這個起家的,后來才做窯爐。
劉: 他沒在佛陶待過吧?
盧: 他在耐酸廠干過,他跟我們搞設備,幫我們工廠搞設備,搞球磨機等等。
劉: 他是不是耐酸廠的員工?
盧: 不是,他是臨工,我們工廠要什么設備他就幫我們搞。說他是臨時工也不是臨時工,他是個體戶,也不是耐酸廠的員工,反正你說要搞什么他就幫你搞。
劉: 算包工頭?
盧: 后來就是包工頭。
劉: 你們小組中,后來有沒有做設備的老板?
盧: 有,陳中治現在是私人老板(搞設備),霍達忠現在也搞五金加工了。
劉: 盧勤那個時候還沒來嗎?
盧: 盧勤是建陶廠的。
劉: 他沒參與過第一條生產線的引進吧?
盧: 沒有參與過。
用水煤氣燒有顏色的彩釉磚是打破世界難題的勝利
盧: 除了剛才我所說的,另外一個風險,是煤氣的質量。伊力奇說我們中國天然氣沒有,液化石油氣也沒有,只能用人工制造苯水煤氣。因為要把煤變成苯水煤氣,我們要到山西陽泉買無煙煤。其他煤不行,燒出來硫的成分多,粉塵比較大,不能燒陶瓷產品。只能用無煙煤。無煙煤燒出來的硫,和二氧化硫,這些東西對陶瓷產品是有影響的,特別是紅色、黃色、綠色,燒出來以后會變其他顏色。所以硫的成分是關鍵。所以伊力奇派來的專家說:你們一定要控制硫的含量……水不是主要矛盾,灰塵不是主要矛盾,硫才是主要矛盾。后來我們到工業廠請來一個專家,教怎么除硫,這是技術關鍵。用水吸收,除去一部分硫,叫水滌法。這樣燒出來的產品顏色不會改變。
劉: 你的意思,無煙煤燒出來也要除硫?
盧: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供銷科,有一個專門的副科長去山西買煤。買回來的煤是一塊一塊的,把它打成粉,再做成球,燃燒。
后來我們的水煤氣過關了,意大利的專家也很感動,說:你們用水煤氣燒有顏色的彩釉磚,是打破世界難題的勝利。他說:我們以前沒有做過這個工作。外國很少用這個辦法去燒瓷磚的,他們是用天然氣或液化氣。
劉: 當時他們判斷你們用水煤氣也能燒?
盧: 也能燒,但他們沒有把握,他們不清楚生產出來能不能滿足這個指標。
劉: 那他們也是經驗不足啊。
盧: 他們沒有。所以他說“你們做了我們意大利沒有做過的工作”,這一點是我們值得驕傲的。
劉: 是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天然氣嗎?
盧: 沒有,也沒有液化氣,1981年的時候哪有啊?
輕工部支持,2.8:1換回首期貨款20多萬美金
盧: 1983年我們安裝一年,到1984年投產,當年5月5日第一片磚出來。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利華廠接待的中央首長、各個省市的首長多了,每天都有,專門成立了一個接待室。
利華廠和耐酸廠是一個廠,是用補償貿易的方式弄出來的一個廠。因為你耐酸廠是國營廠,利華廠是補償貿易的廠,是為這個新設備的引進開的新廠。是用“三包”的補償貿易的方式去搞的。
我們那個時候用207萬元買設備也不簡單,我們廠沒有美金,公司也沒有美金,那美金怎么解決呢?我們到北京去,到輕工部用2.8元人民幣買1美元,把美金買回來。我們比市場便宜很多,按市場價來我們受不了,市場最高匯率是13:1。
劉: 你們要自己付美金?不是用香港的美金嗎?
盧: 香港的美金我們是用補償貿易的方式抵的,但第一次給錢還是要用美金的。30%的首期,20多萬美金,我們大概用70萬元人民幣去買。當時產品沒有出來,怎么用補償貿易的方式給人家?政府用2.8:1的匯率把美金賣給我們,我們把人民幣給他(政府)。
劉: 那你們怎么能夠用2.8:1的匯率把美金買到?
盧: 我們去北京的輕工部,因為我們是全國第一條引進的生產線,爭取政策優惠,支持我們。
劉: 算是國家補貼了你們?是進口補貼性質。
盧: 國家對我們很優惠。我們是第一條全部引進的生產線,國家所以要補貼我們。而且我們還要冒很大的風險,花了這么多錢,失敗了怎么辦?失敗了我們企業要負責。我們工廠每年賺了錢要向國家上繳的。所以周總找我去:老盧,你去把這個東西搞好,搞得好不好你自己負責。這個搞失敗了,幾百萬怎么去還債?所以這個風險很大的。當時周總找韓美權,他是廠長,我是技術科長,周總問他這個生產線放耐酸廠行不行。當時他沒回答,回來后找我們幾個商量:這個風險很大,搞不好就很麻煩了。好幾百萬,弄不好我們不好交代,周總也不好交代,怎么辦呢?只能我們把這個弄好了。
(周: 開始是選擇化陶廠,因為化陶廠內后面有一個低洼帶,有個很大的魚塘,廠長是霍華,他年紀大了,不敢冒風險。我就找張銘昌,一去就拍胸脯:行,周總你交給我,我來干。所以后來就轉到了耐酸廠。我心里就放下大石頭了。衛生陶瓷,開始是準備放到工業廠的,原來工業廠是靠近山崗的,8條窯,舊的,全拆掉,再來搞衛生潔具引進。劉熾(音)怕。后來于飛來找我:老周,你還不引進衛生陶瓷?他要把我調去高明。這是1987年左右的事。
劉: 要你去搞衛生陶瓷?
周: 是呀,當時于飛是市長。
劉: 后來是副省長?
周: 當時是大市(大佛山)的市長。
劉: 后來那條衛生陶瓷的生產線是引進到建華廠了?
周: 就是因為那個廠長劉熾(音)呀,后來他到了香港去,他怕失敗。就轉到建華廠去,那個廠長陳細照也是很急,他跟張銘昌一樣,說:給我,我們去干!結果很快去考察,考察回來就干。
劉: 建華廠引進了第一條潔具生產線?
周: 也是全國第一條。
劉: 建華廠后來劃歸鉆石了?
周: 那是后來,鄭培生以后。
劉: 建華廠很多人出來做了潔具,比如樂從的樂華/箭牌,很多人是從建華廠出去的。
周: 霍業新,也叫霍新,就是謝岳榮的岳父。他是建華廠的技術科長。
劉: 所以一溯源,整個潔具也是從石灣出去的。所以佛山陶瓷史就是石灣陶瓷史,它是根。
周: 衛生陶瓷最早是唐山搞的,我們建陶廠曾十到唐山。引進之前,建陶廠也做潔具,手工做的。唐山也沒有全線引進,它是單機引進的。所以我們是第一條生產線全線引進,國內都沒有的。劈開磚也是我們第一個引進,琉琉瓦也是我們第一個引進的,彩釉馬賽克也是我們第一個全線引進來的,釉面磚也是,基本上建筑陶瓷這些品種都是我們引進的,這樣才不斷地擴大。我們那些人也是自由的,有些人在佛陶做,有些到外面做,你也擋不住他技術往外傳。佛陶的作用就是這樣。)
石灣陶機用消化吸收取代全線引進
劉: 盧工的事還沒講完,耐酸廠引進完這條生產線后,還引進了什么?
盧: 后來我們就是消化吸收。
劉: 就再沒有整線引進過?利華廠后來有幾條線?
盧: 后來發展到8條,都是自己搞的。耐酸廠跟利華廠加起來8條。我自己在耐酸廠搞了生產線以后,伊力奇有天到工廠找我,他問我工廠情況怎么樣。我說買了他們公司生產線以后,就自己搞了,搞了很多生產線,總共加起來有好幾條(我沒跟他說有8條)。他說:你帶我去看看行不行呀?我覺得老關系嘛,就帶他去看。他說原料這方面不看了,就看成型和燒成。看了壓機他沒說什么,后來帶他看輥道窯,一進輥道窯他就罵我了:你這個輥道窯和我的輥道窯是一樣的,你怎么搞的?他通過翻譯跟我說的。我說: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設計的,我們的結構和你唯高公司的結構是有區別的,你不要看外表,外表和你們唯高公司的可能有一點相似,但里面的結構、噴嘴的布置、風機的位置、煙囪的高度和你完全不同。他說:你在中國有沒有申請專利?我說沒有。我反過來問他有沒有在北京申請專利?他說也沒有。那我就放心了。我說沒有關系呀,反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后來他也沒說啥。
劉: 你自己搞的窯爐,壓機用誰的?
盧: 買過一些,唯高、薩克米都有。窯爐是自己搞。
劉: 那個時候力泰還不行嗎?
盧: 還沒有起來。
劉: 力泰是九十年代才起來。
盧: 后來它發展快,那個時候……
(周: 他那個生產線,省計委因為是一個樣板,很重視。我們的補償貿易商,董事長姓王,他跑掉了,可能是因為經濟有問題。我們沒辦法,他沒能力去銷,我們也要還債的,外匯要還債的。我們跑到省計委去,跑到北京,結果給了2.8:1的匯率,給了我們30%的首期,后面的直接補償。)
盧: 對我們支持很大。所以利華廠不用市里面出面,很快把錢還清。建華廠那條線生產的產品,有出口出有內銷。
劉: 你們后來的窯爐都是自己的?
盧: 除了窯爐以外,其他如球磨機、壓機,陶機廠可以生產了,輥棒研究所可以生產了,其它一些小設備很多工廠都可以生產了,現在已經國產化了。石灣除了引進生產線以后,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綜合考慮,足不出門,我們整個陶瓷生產設備,硬件、軟件,全部自己解決。很多老板、民營企業家都冒出來了。
整線引進對行業影響巨大
劉: 后來你們在產品生產、設計上,做了什么對行業有影響的重要的產品嗎?
盧: 上一次,佛山政協找我和周總,我談過,引進生產線影響是很大的,剛才我們兩個談了幾點看法:
第一點是促進了我國建陶的機械化、自動化。我們以前生產是半手工、半機械的,自從引進這條生產線以后,從原料進來到產品出來,都是自動化的,燒成從24個小時變成1個小時,工人操作就是看看儀表看看設備。生產自動化這一點對我國建陶影響是巨大的。
第二點,大大縮短了建陶的生產周期,以前從原料產品出來一般要經過7天,現在2天左右。
第三點是加快了我國技術工藝的進步。我剛才所說的硬件、軟件,我們技術水平提高了,我們利用外國的技術把我們生產陶瓷的工藝改善了,趕上了世界的先進水平。
第四點是大大降低了占地和勞動強度。以前干陶瓷干得汗流浹背,勞動強度很大,很苦,現在引進生產線以后,工人在那看看儀表,看看操作,這里看看,那里走走,這個生產線就可以生產了,工人勞動強度降低了。所以利華廠引進第一條生產線以后,工人對我們說:你們和周棣華做了很好的一個工作,我們現在不用那么苦了。以前我們整天干活很苦的,環境不好,灰塵也大,成天抹汗,進窯爐以后頭發都是硬的。你們周棣華做得好,你老盧也干得不錯,你為我們工人謀福了。這一點,工人是非常感激的。
第五點,提高了我國建陶的裝備水平。沒有引進之前,我們的窯爐是沒有生產輥的,大的球磨機30噸、60噸的都沒有看過,我們的生產廠房比現在寬很多了,噴霧塔是一天60噸。自從我們成立一個消化吸收小組以后,外國所有生產陶瓷的設備,自己能生產出來了。
第六點,縮短了我國建陶生產與外國的差距。假如我們不把這條線引進來,我們還是老樣子生產,還是用隧道窯燒,24小時才能出來,壓機還用手動。引進生產線以后,我們設備改善了,生產速度也快了,我們和世界的差距縮短了。所以后來有人問我:老盧、老周,你們引進以后,究竟和外國有什么差距?我說,差距應該是越來越小了。拿兩片磚放在一起,翻過來看坯底,看得出來,稍有差距,再翻過來,一片是中國產的,一片是意大利產的,證明我們的產品與意大利、西班牙的有差距,但差距很小。
最后一點,引進生產線以后,樹立了我們國家的樣板生產線。我們利華廠在周總的領導下,夠膽把它買進來,國內八個產區都跟著我們引進設備,有些和我們一樣全線引進,有些是買個別零件、個別設備、部分部件,所以這條生產線引進以后,對我們國家影響是很大的。沒有這條線的引進,可能今天的建陶行業也不會發展這么快,也不會有今天的陶瓷大國。我們現在的產量已經把意大利、西班牙拋在了后面,但是我們是建陶生產大國,不是強國,我們和意大利、西班牙還有差距。
周總夠膽把這個生產線引進來,對我國陶瓷行業影響是巨大的。所以中國陶瓷百年史,有周總的名字在里面,是名符其實的。佛陶是黃埔軍校,培養不少人才。硬件、軟件,我們佛陶在建陶行業來說是走在全國前面的。
佛陶集團一年推出幾千件新產品
劉: 1990年你在佛陶做了副總以后,也是管生產、技術和產品開發,你覺得1990年以后佛陶集團在產品和技術上還有什么貢獻沒有?
盧: 第一個是加強產品的開發。我從1990年進公司當副總,1999年退休,9年都在抓生產、技術、科研,每年都有幾百上千的新產品開發出來。抓新產品的開發,這一點是比較成功的。每一年我們都對公司屬下的企業進行評比,每一個企業每一年都有新產品。你沒有新產品出來,你的企業就落后。搞了個“四新”產品評比。
劉: “四新”產品評比是哪一年開始搞的?
盧: 1988年已經開始了,我在工廠的時候已經開始了這項評比。我把每個工廠的技術科長、技術副廠長找來,我同他們開會,究竟今年搞什么產品,你們有什么想法,你們準備搞什么新產品,這是一個內容。
第二個,搞企業管理。企業管理是個軟件,下面很多工廠干活都是很積極的,但是你怎么把它管好,成立一套規章制度,這是一個難題。所以我和周總去意大利考察的時候,也考察他的協會究竟是干嘛的。工廠更難管,所以我們陶瓷公司成立了一個企管部。我在工廠干了10年廠長,廠長干什么?左手抓供銷,右手抓財務。
第三個就是科學研究。我們各個企業都有科研所,特別是比較大的工廠,他們自己有科研室、科研所、科研中心。就像我們佛陶集團有技術中心,建國廠有省直管的技術中心,工業廠有個科研所,各個工廠都有自己的科研所、科研室,最小的工廠也有個設計組。我們就把這些科研所、科研室組織起來,有時候是去外省參觀學習,有時候到外國考察,在公司的領導下去考察一些科學研究中心。我們集中簽定了合同以后,利華廠也組織了8個人到意大利去實習,有霍達忠、鐘光超、陳中治、黃福林等人。
劉: 我的意思是,在你印象中,你抓產品的時候,開發出什么對行業有影響的產品?
盧: 那個時候產品的變化,一個是規格,從生產100mm×200mm的,后來生產1000mm×1000mm的,生產的規格大了(現在可以生產1000mm×2000mm的)。那個時候,我們還可以生產800mm×800mm、600mm×600mm的。另外,花色品種比以前豐富多了,以前一個品種就一個顏色,現在各種顏色都有,顏色多樣化了。磚也變薄了,以前的磚厚,800mm×800mm,起碼是1.2厘米厚,現在0.9厘米就可以了。生產的磚越來越薄,省原料,省能源,成本降低,工廠可以多賺一些錢。另外一個,輥棒的研究——在研究所,那個時候輥棒已經開始生產了,但是生產出來的直徑比較小(直徑就是30、50)、長度比較短,那個時候只能生產一米、一米二,后來生產直徑大、長度比較長的,現在長度可以做到三米四、三米五。
我們一年有幾千個新產品出來,一年評比一次。我們還在公司內部搞技術交流,比如哪個搞了什么新的產品,除了需要保密的不說,其他的都可以說。我們把下面工廠的技術廠長、技術科長、科研所負責人請來,講自己的新產品是怎么生產出來的。核心技術可以不說,但產品可以交流,這種交流在我們公司很受歡迎。
瓷磚從紅坯到白坯的轉向是錯誤的
劉: 你原來在利華廠的時候,那個時候生產什么產品?
盧: 利華廠引進第一條生產線以后,全部生產彩釉磚了。剛才周總說了,1978年的時候我們形勢不好,1978年我們第一片彩釉磚生產以后,各個廠都來了,大家都生產建陶了。
劉: 彩釉磚在市場上流行了多久?
盧: 彩釉磚現在也有。
劉: 彩釉磚是不是仿古磚的前身?
盧: 仿古磚是后面才有的。彩釉磚是紅坯的,后來改成白坯的。
劉: 其實從紅坯到白坯,這個轉向是錯誤的。
盧: 錯誤的。
劉: 一下子把好的原料燒掉了。其實最早就是用的紅坯磚。
盧: 所以陳帆和我都主張用紅坯。
劉: 后來紅坯回不去了?
盧: 回不去。
劉: 是在哪個節點上轉成白坯的?應該是從佛陶開始吧?
盧: 很早了。
(周: 紅土作原料,當時是這樣的,沒有那么大的量,不夠挖,有時還打架的。我家鄉的紅土挖得差不多了。)
劉: 紅土在廣東算好的土嗎?
盧: 紅土在廣東是很多的,那為什么轉白坯呢?因為有很多外國的產品進來了,我們拿著反過來看,是紅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是紅坯的。不過它不完全是紅土,高檔的產品是白坯的。紅坯低檔,價錢賣不起來,所以轉成白坯的。白坯成本可能高一點,但賣價更高,算一下,還是有利可圖的。(周: 紅坯吸水率高。)產品強度不高,作為墻磚,吸水率高,不容易掉下來。但是鋪地呢,因為強度不大,掉個錘下來就會打破。
劉: 可以用兩層吧,坯下面再來一層。
盧: 也不行。
劉: 你不是底坯用紅土,上面那一層用白坯嗎?
盧: 白土一個配方,紅土一個配方,那更復雜了。
劉: 那西班牙的紅坯磚是怎么做的?
盧: 它全部是紅坯。
劉: 怎么做效果?
盧: 它是復合土,底坯是紅的,在上面加一層復合土,是白色的,在白的上面再加顏色就可以了。
劉: 這樣瓷土原料可以省很多的。
盧: 所以陳帆極力主張用復合土。
劉: 后面返不過來了,沒人做?
盧: 現在已經固定下來了,歷史不能重演的。
劉: 這個成本更低吧?
盧: 低。但強度低。
(周: 現在用的都是硬質料,紅土變形率高、收縮大,燒成率低。我認為紅坯被白坯替代,是一個技術進步。不管陳帆怎么說,怎么說都是用硬質料好。硬質料一個是硬度高,強度高,燒成率高,但有一個大問題,成本高。)
劉: 什么時候轉過來的,彩釉磚時候是做紅坯的?
(周: 我告訴你來源是什么,當時都是用紅泥來做的,紅泥拉到南海,交警意見大得很。要到松江那邊去拉。松江也沒有多少,物資公司的原料人員到龍門縣去,瑤族人聚居區,有一個鎮,那里有鉀鈉長石。)
盧: 現在用瓷沙,鉀鈉長石成本高。
(周: 回來用破碎機,破碎之后再用研磨機研磨,再經過噴霧塔,形成空心顆料,小球形的,一壓就排氣,它的分子組成里面是有孔的。當然,紅土也一樣可以壓。市場上要求用白坯,一出來后很吃香,市場決定的。)
(本文未經受訪者本人訂正)

盧敦穆拿著照片回憶往事
人物簡介:
盧敦穆,男,漢族,中山縣小欖鎮人。1947年讀小學,1953年讀初中,1956年讀高中,1959年就讀廣州華南工學院(專業為化工);1964年畢業分配至石灣耐酸陶瓷廠,歷任職員、設備科副科長、科長,1983年升任副廠長,1984年任廠長,1986年兼黨委書記;1990年升任陶瓷公司副總經理,分管生產、科技、技術;1999年退休,同年12月18日任佛山陶瓷工業協會首任會長。

 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頭條焦點
頭條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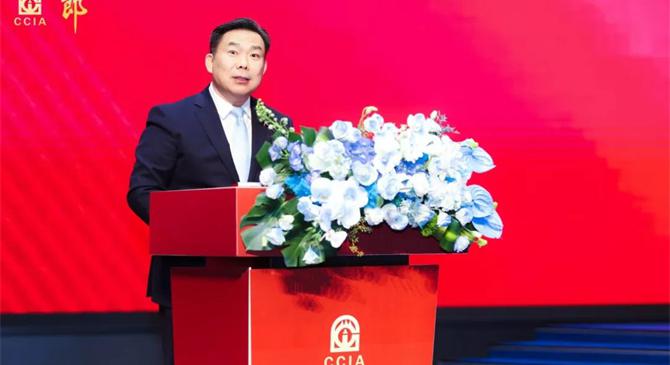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