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訪者:馮紅健(廣東特地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長)
采訪者:劉小明(華夏陶瓷網總編輯)
整理者:申志(華夏陶瓷網首席記者)

行業人都知道馮紅健喜愛打高爾夫,而且是公認的高手之一。
關于高爾夫,坊間流傳著的一個故事是:2004年的某一天,一位朋友買好了裝備把他拉到球場,并引見一位教練,然后丟下他就走了。令這位朋友沒有想到的是,馮紅健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徹底迷戀上了高爾夫。
據說,馮紅健最勤的時候,每天都去打9洞,6點半起來打兩個小時,8點半打完,9點半到公司。最多的一年竟然打了足有200多場。
高爾夫打多了,自然也就有很多體會。比如,他曾經說,“球要一桿一桿來打,事要一件一件來做,做錯做對都是自己做的!”這一理念似乎也吻合2004年以來特地陶瓷養成的個性,從容、淡定,不求規模、速度,惟求有增長的質量。
生意場和球場都是名利場。只有對規則和禮儀尊重者才能贏回同樣的尊重。在公司內部,作為董事長的馮紅健嚴格遵守現代公司“委托—代理”制設定的“一米黃線”,日常經營活動很少直接參與。他與“管事”的總經理——“少帥”李強之間的這種默契在行業中罕見。
職場上的馮紅健為人謙和、真誠,尤其善待媒體,對記者們的工作總是盡量配合。這也使得他成為行業中曝光率較高的企業家之一。他也樂于用這種方式承擔特地陶瓷代言人的角色。
然而,如果不細究,你確實很難想像那個總是在高爾夫球場揮灑自如的馮紅健曾經還是一個名牌大學的工科畢業生,一個國有企業兢兢業業頗有建樹的技術員。更難想像他還是一個在體制內“搞地下工作”的叛逆者,一個創業非常期對目標客戶實施圍追堵截,非常搏命的推銷員。
馮紅健幾乎是準點到達季華路創意產業園辦公室接受記者采訪的。8O后的美女同事帶著一臉的好奇陪我們一起聽完了老板年輕時候的創業故事。但問她對老板的印象,她只說:他很時尚!
對于一個6O后的“大叔”級人物,這無疑是晚輩相當高的評價。
重點中學比別人多讀兩年書
劉小明(以下簡稱劉):最近我在做“佛山陶瓷30年”的系列訪談,打算采訪50個行業資深人士、企業家、專家、學者,希望將來還能出個訪談錄。明年在這個訪談基礎上加上自己入行十年來搜集的資料,還會啟動產業史《佛山陶瓷30年》的項目。科達這一塊,我跟吳躍飛、吳桂周做訪談的時候有所涉及,接下來還準備訪問其他關鍵人物如鮑杰軍、邊程等。在創業元老中,你是第二批去科達的吧?如果說盧勤和鮑杰軍他們是第一批話。鮑工那里到時我會跟他談的。
馮紅健(以下簡稱馮):其實鮑工也是后進的,前面是盧勤跟黃國權。不過他們三人可以算是第一批的。
劉:我就是想請你從自己的角度談談科達的歷史。
馮:建陶廠的經歷也可以談。
劉:對,對。建陶廠那邊,我跟劉孟涵談過一次。最近宏宇在贊助搞“石灣陶瓷史”,也拉了我參加,佛陶集團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塊。科達這塊,要還原全貌,必須要把主要的當事人都找出來,把碎片拼成全貌。我覺得你是“科達系”一個貫穿式人物,從佛陶到科達、歐神諾、特地……你是能把很多事情貫穿起來的關鍵人物之一。先請你談談入行前的一些經歷吧。比如,先介紹一下你讀書的經歷吧,你是哪個中學畢業的?
馮:陽江一中。我是1966年出生,華中工學院84級應屆生——我在武漢讀書。我們書多讀了幾年,我們是第一屆趕上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應屆畢業生,虧了2年。
劉:這個我知道,那年我們縣中也是這樣的。但我一直以為你是景德鎮陶院畢業的。
馮:哪里啊!那年上高三,全國重點中學都是這樣的,但非重點中學不是這樣,還是讀到初二、高二就畢業。我們初三、高三是沒書的,當時課本還沒出來。
劉:我是83級的,我那年考理科沒考上,后來轉考文科考上的。
馮:在華中工學院,我們是瞧不起83級的(笑)。
劉:因為我們是回爐的嘛(笑)。
馮:不是這個意思。我們這一屆剛好跟83級的宿舍在一起,他們是非重點中學畢業的,按道理他們要晚我們一年的,結果還早我們一年,成了師兄。但各種表現我們更勝83級的。
劉:你學的什么專業?
馮:自動化儀器儀表。
劉:華中工學院那個時候是很牛的。
馮:華中工學院是排在清華、北大之后的重點大學,地位還是蠻高的。
劉:我記得華中工學院那個時候有個新聞系,而且非常厲害。
馮:就我們那一屆開始有新聞系。
劉:我原來在中山,有兩個同事是華中工學院來的。現在江門新聞界的主要負責人,電視臺的,報社的,都是華中工學院新聞系出來的。當然,現在華工的新聞系弱了,畢竟它是理工學校,不過早期輝煌過,尤其是八十年代。
馮:我們原來確實很吃香的。

選擇佛陶集團因為可自由擇業
劉:你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哪里,直接到佛陶嗎?
馮:我1988年畢業,當時佛山市人事局來招聘,學校有個特殊政策,即允許20%的畢業生自由擇業。
劉:當時是包分配的哦?
馮:改革好像是從我們這屆開始。所以華中工學院在我們畢業之前,找了很多市(人事部門)的來招聘,只要跟他簽了協議,就可以跟著走,檔案直接投出去了。我們了解佛山,本身是廣東人嘛,沒選廣州、深圳,因為感覺那些城市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了,佛山是中等城市,還有發展空間。前天我去佛山迎賓館住了一晚,因為佛山市陽江商會成立。其實那個地方就是當年人事局放檔案的地方。畢業那個暑假,我把檔案給了佛山人事局,然后回家。回到佛山之后,到人事局拿檔案,人事局也不知道把我分到哪里。當時化纖、電子、塑料、陶瓷行業是最火的,他們拿了一份表我。之前我了解過佛陶集團,陶瓷雖然苦,但開始有景象了。我于是選擇去佛陶,拿了檔案,直奔佛陶大廈。
那時佛山人看不起石灣人的,石灣那時還是鄉下,從城門頭走回去要一個小時,周圍還是田哩。
劉:你是走路去嗎?
馮:搭車的。走路是晚上,白天不會走路的。
建陶廠對大學生非常好
劉:佛陶大廈當時已經建起來了嗎?
馮:建起來了。當時人事部和團委在一起。幾十個廠報上來,要大學生。大學生分配下去,一個廠也就兩三個。我看中了建陶廠(石灣建國陶瓷廠),因為是省直管企業。劉孟涵當時當廠長,我打了個電話去,劉孟涵的辦公室有一個陽江人,劉孟涵就說,“那你去接吧,你們是老鄉。”我當時挺感動,他還派車去廣州幫我拿行李。
劉:他為人挺好的。
馮:我托運的全是書,丟在廣州火車站,哪里拿得回來?后尾廂全是書。
劉:我看你挺喜歡運動的,在學校的時候喜歡讀書嗎?
馮:還可以吧。
劉:那些書現在還在吧?
馮:應該還有。
劉:當年從陽江考上重點大學,在學校里面成績肯定是拔尖。
馮:前5名吧。現在我們那幫人聚到一起了,用微信建了一個平臺。
劉:就是從陽江中學考出去的那些人?
馮:對,這幫人,都是校友,學校的尖子生,上清華、北大、華中工學院的,現在大家想為陽江做點事,看能否弄個項目什么的。我們的群名叫“蕩起雙槳”。
劉:你剛到建陶廠的時候適應嗎?
馮:到了建陶廠,劉孟涵安排我一個人住一間房。當時建陶廠對大學生挺好的,在我之前應該有三個大學生,其中一個是鄭樹龍,比我早一屆,他現在還是歐神諾的副總裁。他們都是一人一個房間。我當時住不進去了,于是,我被分派去計量室住,等于是一人住了一棟樓。那里有恒溫室,但我不能住恒溫室,就在倉庫里隔了一個房間給我,外面全是電器。那個時候佛陶待遇很好,一來沒兩個月,就發了一套煤氣設備,讓我們自己做飯用,我們那些單身漢經常在一起做飯吃。
我在建陶廠學到很多東西
劉:你是1988年過來,那你算很早了。當時鮑杰軍、吳躍飛還沒來吧?
馮:盧勤比我早,他1981年畢業就來了,我來的時候他已經有很大成就了,是“新長征突擊手”。他在設備科,我在計量科。他在輥道窯上很有造詣,把隧道窯改成輥道窯,是他主持的。以前燒重油,重油不能直燃,要隔焰,用隔焰板把油隔開,上面走產品,這種方式溫度不好上升,不好控制,之后改成柴油可直燒。當時沒辦法,要用重油嘛。
建陶廠是個綜合廠,有馬賽克、彩釉磚(已經出來幾年了)、衛生潔具、園林瓷,四種產品四種燒制方式。為什么說在建陶廠能學到東西呢?因為它什么都有。四個車間(還有一個機修車間不算),四種產品,采取的成型、燒制方式都是不一樣的。建陶廠是佛陶最豐富的企業之一。
劉:劉孟涵說,當時建陶廠是全國建材行業的紅旗企業。
馮:建陶廠擁有歷史悠久的馬賽克品牌——“石灣牌”,這個商標現在毀了,真是浪費。建陶廠曾經連續十多年位列全國前列。在生產方式上,當時的燒制的方式很原始,車間沒那么自動化。當時最自動化的是彩釉磚,是用輥道窯做的,施釉線相對更自動化一些。衛生潔具是引進的德國的設備。園林瓷是比較老的,琉璃瓦,用擠壓成型,上釉后,用隧道窯燒。有幾種窯。馬賽克用隧道窯燒,開始是裝砂砵燒,因為太小了,一顆顆的,用砵子裝起來,然后摞起來裝窯車,這邊推進去,那邊推出來。衛生潔具,也是用隧道窯,像現在這種立式的,也是比較先進的,以前是豎式窯,一爐一爐的,從隧道窯開始可以連續生產,這邊進那邊出。彩釉磚,當時剛出來沒多久,才幾年時間,但最有競爭力,別人說我們建陶廠、化陶廠做磚就是在“印鈔票”。
劉:你當時是否突然覺得自己一下子就比同學們有錢了?
馮:有錢多了,其他同學每月還不到一百塊,我是好幾百塊。
劉:我記得1987年參加工作時我的基本工資才五十多塊錢。
馮:他們說是要宰我。同學中工資高的,一個是我,還有兩個分到電力系統的,在武漢,要去非洲援外的,當時不是支援亞非拉嗎?他們是雙倍、三倍工資,還有很多補助。
劉:那你在建陶廠的收入不斷地漲,是不是很快就過千了?
馮:是,一兩個月就過千了,基本工資加獎金,還有補貼。日常用品不用買,全是發的,洗潔精、洗衣粉、毛巾,錢就感覺花不完。磚做出來不愁銷路,印出來就賣掉,全國沒幾家做彩釉磚的,那時我們最火了。
在建陶廠學到很多東西。我的觀念是,學生來就要學習,你做了才能學到手。當時最怕沒事干。當時整個佛山沒圖書館,查不到資料,對我們工科生來說是致命的打擊。第二年,在禪城酒店對面建了圖書館(原來叫干部培訓中心)。
劉:現在好像叫科技館。
馮:那里是我經常去的。主要就是查資料。那里還常辦培訓班,英語的、考級的。當時佛山大學(現佛山市科學技術學院)剛剛建,也沒圖書館。
劉:那選擇佛山看來也是有問題的。佛山就很小一片,就一個鎮的感覺。
馮:是有問題的。當時佛山就城門頭這一塊,興華商場就是商業中心。
劉:在學習條件方面,佛山跟武漢比差遠了吧?
馮:跟華中工學院差遠了,在學校搞設計是全開放的,電器什么的全都可以買。周壽斌是我的設計導師,后來當過院長,他帶我們做頻譜分析儀,后來到處都賣。“多譜勒”頻譜分析儀,當年是我們的設計課題,我是做分析系統的。
我和盧勤拍檔設計輥道窯早期對行業起過一些作用
劉:你去科達是1995年吧?
馮:是1995年,比吳躍飛晚一兩個月。在建陶廠,后面我跟盧勤拍檔。
劉:你在建陶廠任過哪幾個職位?
馮:我一直在計量室。盧勤1988年已經是“新長征突擊手”,沒給職位他,好像掛了個設備科副科長——一個科里好幾個副科長。我在計量能源科,一直是普通員工。
劉:劉孟涵沒提拔你嗎?
馮:其實我機會是最好的。我第二年就去了團委,負責團委工作。這么早就接觸管理層,對別人來說可能很好了。但我覺得行政管理這里面有奧妙。因為我是黨員,我必須列席黨委會,列席了兩次,我覺得不對勁,我還沒這個能力。
劉:為什么?
馮:我父親是政工出身,是陽江一個公社書記,我從小立志不做這個。
劉:哦。
馮:他是軍人轉業到地方的。另外,我這么淺的資歷,列席黨委會,影響很大。
劉:你可以不表態嘛。
馮:(笑)但你知道了很多東西呀。
劉:也是,你確實是太年輕了(笑)。
馮:于是我主動找到劉孟涵,要回去搞技術。因為我在這里沒根吶。后面是何永標接替我。當時霍達炎是佛陶的團委書記,級別很高。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石灣人,在國營企業很難搞,于是主動提出回去搞技術。
正好,建陶廠搞引進,以前的電器工程師年紀也不算太大,但做事較慢,也不想做太多事,希望把所有活都能給我做。我所在的計量能源科,管能源和技術檢測的。
劉:后來建陶廠也沒提拔你?
馮:沒有。后來設備科分開嘛,設備科搞強電、動力,技量科搞微電、控制,窯爐變壓器還是后面的。這邊所有的事情都壓在我身上,何樂而不為?爽死了!
劉:你在的時候參與過什么項目?
馮:一條做彩釉磚的新線控制系統,還有建陶廠所有窯爐的控制系統都是我設計的。我與盧勤是那時結緣的,他做機械設計,剩下的都是我來搞。當時在廠里是這樣分配的,機械和動力都在設備科,我搞弱電、檢測、控制和引進系統的消化、改造。我后面還出了一次國,結果后來要賠兩萬塊錢給廠里。
劉:為什么?
馮:他說你培訓過,要離開廠里就得賠錢。
劉:去的是意大利嗎?
馮:德國。
劉:當時是引進什么設備?
馮:是李兆峰的整線設備,雙層窯、萊斯壓機。第一臺600噸壓機是建陶廠搞的,力泰在我們的隔壁,擺在后院專門供力泰解剖的,我們不給動的,是佛陶搞研制用的。引進這個項目,我們把彩釉磚的生產線從全自動改為半自動。
劉:這是什么時候的事?
馮:1991年、1992年的事。全線引進的,但要改成半自動,因為不實用。我們的壓機,所有系統后面還有個產品分選,但分選當時在中國根本用不了。
劉:我們現在才提分選。
馮:現在提這個分選、分色就對了,當時太早了。國外當時分選就兩級——優等、不優,不優的當場就敲碎。因為他質量控制得好,98%是優等,2%不優的就不要。第二個,色號不多,就兩三個色號。他們給我們分了四個色號,對方的技術員說四個色號已經很多了。但我們做不到。第一中國老百姓對色彩很敏感,第二我們的控制達不到要求,套色沒那么精準。設備這么好,但前段原料控制不到位也沒有用。
劉:整個系統配不上啊。
馮:這是個系統問題,每個廠從原料開始,都不標準。所以要改。1991年、1992年,開始使用CAD,設備科進了一臺CAD繪圖機,沒人會用,沒人敢用,結果我就來用。本是用于機械設計的,我用在電路設計上,就不用再畫圖了,快了很多。這是一套軟件來的。
劉:從哪來的?
馮:進口的。當時很多設計都是手繪的。中國弱電標準不是很好,引進以后,我就按國外的方式搞,我搞出來后,看起來很明白,一條窯爐一張圖紙就搞掂。
劉:看來你和盧勤等那時候在建陶廠起了很關鍵作用。
馮:應該說當時的盧勤和我,對行業有一些作用。我們這套技術做完后就陸續輸出到全行業,那時通往南莊的橋也建好了,佛陶的技術便加速外流。
建陶廠要開除盧勤黨籍我投了棄權票
劉:回到科達早期創業。科達早期建廠的時候接云南易門工程是個轉折點,那個時候盧勤還在廠里嗎?
馮:當時還掛著。石灣“對海”(南莊)鄉鎮企業跟佛陶合作,我們叫外聯廠,建陶、建國、工業、美術都有外聯廠,搞技術扶持。我們技術部門的人——技術部、設備部、銷售部,每個月都要去其他廠,有頓飯吃的。老板們會定期請我們過去指點一下。當時叫對口支援,雙方交流很頻繁,佛陶下面這么多廠,對南莊或南莊周邊這些新興的陶瓷廠都支持過。我記得我們支持過對面的上元、溶洲(尤其溶洲二廠),還有南海大欖好幾個廠。快到西樵那邊有個村委辦的園林廠,也是佛陶的園林廠扶持的。在建陶廠的時候,我們技術部、設計部、銷售部,每周都要出去吃頓飯,都是那些老板請的。
一開始沒橋時,坐輪渡過去,或者從樂從兜過去。有橋后就方便了,對面很多廠都是這樣起來了。
劉:聽吳躍飛講,佛陶是自己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
馮:有這個感覺。
劉:聽說當時每個廠都有個小金庫,經常發發錢什么的。
馮:小金庫就是收些技術服務費之類的。
劉:哦,體制外循環。
馮:當時,一批人做技術的,我和盧勤,他做窯爐我做自動控制。我們是做得比較出名的。還有建國廠的王褒,他是西北輕工的,專攻壓機。建陶廠有個王明炬,跟王褒合作。鮑杰軍來建陶廠,在他們后面也搞壓機。他們專門幫周邊廠維修壓機,隨叫隨到。壓機對陶瓷廠非常關鍵,后面很多東西都可以人工做,壓機的活不能人工做。賣配件,你要多少錢都有人買。當時一個晚上要壓多少磚?停一晚損失大了去。所以,他們開始做壓機配件,江灣路一條街都是做配件的。
劉:你是什么時候出去的?
馮:我出去與盧勤合作也是有個契機。1992年重慶李兆峰并購的一間陶瓷廠要上馬。建陶廠內部搞了一個窯爐公司,搞這個公司就是因為李兆峰在國內遇到很大的問題,他所有陶瓷廠都不盈利,所以在香港要摘牌,要追究他的責任。他希望改變,所以找建陶廠的人去幫忙。建陶廠就組織了一幫技術人員過去。
劉:李兆峰的公司是什么時候上市的?
馮:1991年、1992年左右吧。那時是建陶廠一個副廠長帶隊,我參加了,沒談成,價錢談不攏。我們談的主要任務是把生產搞正常,經營你不用管。后來就我跟盧勤拍檔去做了這個項目。
劉:重慶那個廠名字很特別,叫什么二丁……
馮:叫“二丁掛”。
在那待了幾個月,回來后,這邊盧勤的事情炒得沸沸揚揚,說他在外面有公司,建陶廠要處理他了,要開除他的黨籍。我記得開會的時候我好像投了棄權票。
劉:那時盧勤在外面有公司了?
馮:1992年前后就在做了,當時是三個人,有一個就是黃國權。最早是做貿易,更早的時候那個廠還做過衣服,我記得1995年倉庫里還有很多服裝。
劉:你說有三個人,那還有一個人是誰?
馮:另一個人沒提了,他不在這一行做,是黃國權的一個親戚。我1990年就開始跟盧勤炒更,我們的BP機幾乎同號,是“樂聲”牌,一起買的,好幾千塊錢,為了聯系方便,晚上找不到人嘛。手機不敢買,BP機揣在口袋,怕人看見,調成震動,一有響動就掏出來看,然后復機,有種做秘密工作的感覺。BP機是盧勤買的,因為我們有個項目在做,他給了一臺我,錢是老板出的。BP機是數字顯示的,我們有個密碼本,520代表什么,要對應著查是什么意思。有代碼的,留言也要用代碼,直接CALL就留號碼。那時候真的很像搞地下工作的(笑)。
劉:盧勤離開比你早多久?
馮:早不了多久,因為那時已經有項目在做了。
劉:盧勤離開佛陶的時候應該反響很大吧?
馮:建陶廠很多人有意見,因為當時不止盧勤一個人,有很多人在外面干事,大家提了很多意見,討論該不該這樣。我走時,是直接把檔案找出來,跟劉孟涵說,要賠多少我賠給你。所以出國培訓的那一項我賠了2萬元。剛分的房子2房2廳也退掉了,在工廠旁邊。
1995年,盧勤接了易門的整線工程,晚上打電話過來,問我要不要出來干。我沒多考慮就答應了,當時感覺在建陶廠確實也沒什么大前途了。
“科達合伙人制”是盧勤設計好的
劉:你是以合伙人的形式加入科達的?這種方式是加入的時候你要求的,還是盧勤主動提出來的?
馮:是盧勤設計好的,進來就給一定股份。我們從公司借錢入股,在分紅里面還。盧勤給的條件是,出來,公司借錢幫你買一套房。
劉:他已經有這個實力了?
馮:有啊。沒多少錢,幾萬塊錢而已,當時房不貴的。鮑工、吳躍飛、我都在公司買的房里住。黃國權跟開發商有關系,先不給錢的,好像以一種什么形式把房子先拿到的,后面錢還是給完了的。房子在江灣路加油站對面,現在很破舊了。沒辦法停車的,只能停摩托車。鮑工的那套房,后來用作營業部,吳躍飛住在樓上,我在他隔壁。科達有了營業部,接洽的時候就有個點了嘛。后面買了江灣立交橋那邊的物業,蒙娜麗莎現在用的那棟的一樓也租用過。然后才到對面去買的,現在好像處理給誰了。我管科達銷售時在那辦公的。
劉:這么說,江灣路那邊有過三個辦公地點?
馮:三個。鮑工那房子,成立了“科達工程技術服務公司”,我們以這個名義接易門工程。之后到環市鎮的郊邊,原來的制衣廠在那,改成做機械。我去那做過廠長,開摩托車上班。當時盧勤有一輛“豐臺”人貨車。
劉:關于科達的事情,你這次談得最完整。
馮:我親身經歷的應該是清晰的。我在郊邊廠的具體事務做得比較多。
劉:吳躍飛后面管廠,你們不是差不多同時去的嗎?
馮:我們是同期去的。盧勤的設想是,電器找我,吳桂周是工藝,吳躍飛——他去三廠做過機加工車間主任,想叫他把機加工管起來。我們拉了王長水過來,他管機械廠生產計劃,還有朱正炎管技術,是鮑杰軍把他們招過來的,都是江西樂平人。
劉:他們兩個來沒進入股東行列?你們最初是5個股東吧?
馮:他們沒做股東。但我去科達后,也不止5個股東了,還有王碧波、吳桂周——他們都是為了易門這個項目來的。王碧波是從湛江一個廠過來的,管原料、噴霧塔、球磨機,吳躍飛管機加工,我管電器,基本上就齊了。再加上原來的三個——盧勤、鮑杰軍、黃國權,七個股東。這是1995年、1996年前后的事。
分家后科達靠賣掉兩臺磨邊機才起死回生
劉:科達早期分家的事你應該很清楚了,那件事影響大嗎?
馮:是1996年分家的,易門工程尾期的時候,黃、王分出去了。
劉:當時為什么要分?
馮:黃國權提出“橋梁理論”。當時他已經有理論了,還是有一定水平的——他認為,我們做企業就是做個橋梁。盧勤不提什么理論,就是想好好做實業。于是就出現了兩個方向。
劉:橋梁理論的核心是什么?
馮:橋梁理論就是說,我們規模不要做大,只做橋梁——機加工生產不做大,可以找其他資源,我們只做橋梁,后期的市場我們把握。
劉:意思是說,我抓住市場,其他東西由別人去做。
馮:他是做貿易出身,提出這個理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基于這個理論,分家時,黃國權要了銷售部和現金,我們把廠全接下來。銷售部包括鮑工那套房。從他這個角度出發這樣挺好的,因為有銷售點了,名氣也有了。盧勤說我們把廠拿下。易門工程正在結尾,拋光機已開發出來了,有一臺樣機在試用,刮邊機、磨邊機樣機也試制出來了,公司正處在一個節點上。
劉:你們要了人和技術?技術都是你們掌握的?
馮:所有的技術、圖紙,分兩份。因為所有的東西已經出來了,拋光機、刮邊機,拋光生產線都基本成型。拋光機有臺六頭樣機,在華業陶瓷廠試用。當時把易門的圖紙全部分了,大家好合好散。我們惟一有的,就是廠里還有兩臺磨邊機,是現貨。但我們還欠黃國權的錢,凈資產也就幾百萬。他們占約30%的股份。當時我們沒現金,是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這兩臺機器賣出去。但當時我們留下的人沒人做銷售,公司之前都是黃國權在做銷售。
劉:他是南莊人?
馮:石灣人。他跟南莊這邊很熟。
劉:兩臺磨邊機賣出去了嗎?
馮:河南新鄉王牌陶瓷廠(是個勞改工廠)來買磨邊機——那個廠都是勞改犯在做事,沒什么成本。我和鮑工去談,談了三天三夜。他知道我們分家了。等于三家在搶這個單,黃國權,我們,還有馬寶虎——也是西北輕工出來的,他在南莊搞了個組裝廠,也賣磨邊機。馬寶虎在建陶廠待過。我們三家談,價格壓得很死。我們堵了王牌的人三天三夜。在江灣立交西南面的酒店,隔壁原來是交路橋費、車船稅的地方,石灣賓館的斜對面,在鐵軍公園南面,佛山大道的對面。最后我們就在那里成交了。
劉:像貓捉老鼠一樣?
馮:三家談,價格差不多,但我是現貨,擺在這里,可以馬上拉走,他們兩家只有圖紙。其實他是以其他兩方來壓我們的價。我和鮑工,最后拉著他到中國銀行,用他的信用卡,刷了三萬元定金,安心了,解決了。這是科達發展過程中最經典的一個故事。這單買賣一成,基本上把整個廠盤活了。我們賣了兩臺,一臺二十幾萬,正常市價是25萬,實際上賣了20萬左右,還加了不少東西。
劉:回款50萬,基本上就活下來了。
馮:先回款幾十萬,給6成左右,我們活下來了。那是活命的錢啊。我們真的沒錢了,抽空了。企業是這樣子的,看起來賺了錢,工廠在正常運轉的時候不覺得,一停下就不值錢了。
科達買地建廠是因為怕沒有根
劉:那次變故確定了盧勤的大股東地位吧?之前他們三個都是一樣的股份。
馮:鮑工是盧勤引進來的,股份也是盧勤給他定的,鮑工肯定聽盧勤安排的。他說服黃國權給鮑工三分之一的股份,開始黃國權和盧勤他們是各50%的股份,鮑工進來后便稀釋了一次。我們進來時就順理成章了,他們三個同步變為20%。鮑工也管過一段時間的銷售,他可能感覺不對,后來搞拋光線,主抓技術,黃后來就提出分家。
劉:你們是什么時候搬遷到陳村的?
馮:從分家的陣痛中緩過勁來之后,生意一路很順利,盧勤于是就提出買地建廠。
劉:分家后的你們的股份構成是怎樣的?
馮:他和鮑工還是一樣。我們不在意這個事,按原比例擴。
劉:后面還是調整了一下吧,盧勤比鮑杰軍股份要多一點。
馮:應該沒調整。包括邊程過來,大家也是同步調整。
劉:當時為什么要買地?
馮:可能覺得沒有根吧,所以買了陳村那塊地,就是1996年分家后沒多久。華業陶瓷廠,第一臺拋光機是他們買的。分家后,我們把拋光線整線做出來了,21頭。瀾石的鴻業陶瓷廠,溫州義烏人搞的,買了整線,但他老坑我們。
劉:華業廠在哪里?
馮:華業是私拋廠,在蓮塘,第一家用我們的拋光機的廠,我們試機就在那。
劉:第一臺磨邊機是誰買的?
馮:順德的,那家廠的名稱記不清了。鴻業是買的第一條整線,共計2條,200多萬一條。當時進口一條要1000多萬,價格是我們拍腦袋拍出來的,大概進口三分之一多一點就可以賣了。所以我們大約250萬一條。
劉:反正是有得賺。你們真是趕上了好時代,完全是被市場強大的需求牽引著走。在市場機會來的時候,你們又剛好上了大學,讀了相關專業,又在佛陶干出了經驗,不像現在的年輕人這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馮:也許是吧。整線賣掉后,要找新廠,我們找到陳村花卉世界。一開始我們在郊邊那里是一棟棟廠房租過來的,一棟搞機加工,一棟搞組裝,慢慢把那地方都租完了,工廠還是顯得小。鴻業那邊定的線要出廠,都不知道怎么弄出去。花卉世界那里是直接買地,當時政府的付款條件好。我們這邊有廠,那邊是魚塘,還有田。盧勤說一定要買。買地建廠時,碰到一個做基建的,姓陳,我們叫他“煙斗”,他愿意帶資建,是本地一個小建筑商,錢讓我們分幾年還。
劉:這么好條件啊。
馮:就這么巧啊。后面很多事都是給他做,主要是前期的廠房、宿舍都是他建的,因為結了緣嘛。但科達現在的大型廠房跟他沒關系,
劉:陳村那棟辦公樓也是他建的吧?
馮:是他建的。
劉:上市之后那棟樓?
馮:那不是。原來的廠房也簡單,辦公樓就幾層。
新中源下單包產原來是想壟斷市場
劉:你們那棟主辦公樓是啥時建的?
馮:那棟樓過了幾年才建的。那個時候公司發展很快,“煙斗”的錢,三年不到就還完了。賺錢太快了,都不知道錢是從哪來的。我們拋光線一出就不得了,太多事做了。新中源一訂就是十幾臺,而且他們要求一個字——“快”。不過他們沒提完貨,提了他們也沒怎么生產。
劉:他們是想阻止別人買線?
馮:對了。當時只有科達一家做拋光線,他們看準這一點。買磨邊機,一簽就是十幾套。上世紀九十年代水晶磚火過一段時間,這款產品其實不耐磨的,一年磨完就花了,但在鄉鎮市場受歡迎。這種產品磨邊也很好磨。新中源一口氣訂了十幾臺機子。霍熾昌喜歡晚上去現場,要盧勤也到現場去,而且是馬上要去,但這是大客戶啊,盧勤只得依著。現在回想起來才體會到,霍熾昌定那么多貨其實是為了壟斷市場。我們一個月就能出兩臺機。所以,新中源那個時候擴張很快。
劉:真是高人啊。
馮:你想想,在那個時候,從毛坯磚到拋光磚,賺多了好幾塊錢。
劉:其實2005年科達跟他們合作做“超潔亮”,簽約也是帶有市場保護性質的,保護期一年還是半年。所以,我想也是這種思路的延續吧?
馮:我們當時也有疑問,為什么他買了不用?又天天給電話我和盧勤,要裝機。
劉:其實這樣對你們是不利的,你們應該賣多些人。他把你們鎖定了。你們畢竟是知識分子辦公司啊(笑)。
馮:我們確實是后來才反應過來。有幾樣新中源做得都很絕。比如,過了兩三年,他要用舊的整線跟我們換新線的。我離開科達之前,收了一批,補了點錢給他們,他們整線都換代了。新線效率高很多。舊線修修補補還可以用,但效率不高,250萬一條線,50萬收回,我們收回來也值,因為框架還是好的,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改成新線。這樣依然有其他客戶買。拋光線主要是模頭的問題,還有旋轉速度不一樣,效率就不一樣。
科達上市是為了拒絕潛規則
劉:科達當時為何那么好效益,還要上市——這是早期盧勤的夢想,還是邊程來給大家洗腦的?
馮:他們兩個的影響都有。當時我們有這樣一種心理,在中國辦企業有風險。企業要盡可能滿足政府的需求,有很多潛規則的問題我們避免不了。
劉:你們有點不合群。
馮:對于我們來說,只能說盡量做得最好。
劉:如果上市就很規范化。
馮:當時想合法化,惟一途徑是上市。盧勤找邊程過來,就是這個目的。他在佛陶就操辦過上市的事情。
劉:對,在佛陶就是搞這個事,后來到鉆石也是搞這個事,只不過都沒有成功。
馮:盧勤找他來,就應該是動了(上市)這個心思。
劉:這與盧勤本身不愛公關有關吧?他的性格,話都不愿多說,讓他跟政府去打交道……他肯定希望把事情變得更簡單。
馮:關鍵是要合法化。
劉:怎么理解這個合法化?
馮:上市公司所有來源都要公開化,這樣就能拒絕潛規則。
劉:你今天談出了一個邏輯。我明白了,最終這跟盧勤的性格有關系。
馮:上市,我們這幫人變動比較大。1999年,盧勤北京學習完,我是2000年第二批去學習的。順德市委組織部在清華大學辦了個MBA課程班,找人去讀。盧去聽了說很好,于是讓我們所有人都過一過。我和黃建起是第二批,鮑工、吳桂周是第三批。把這幫工科的人,弄到管理學院去學四個月,住在清華繼教學院,三人一個宿舍,對提升我們對管理的認識起了很大作用。回來后我們會看報表了,原來是拍腦袋決策,現在不了。學校的師資也很好,厲以寧也給我們上課。一人幾萬塊錢,集中吃住,全脫產。那個班對我們有作用,對推動上市有作用。
陶瓷行業的經銷商制是邊程搞起來的
劉:邊程是1998年到科達的?
馮:邊程是1998年搞實驗工廠(歐神諾前身)的時候過來的。他對歐神諾早期策劃、銷售有貢獻。
劉:他的第一站在歐神諾?
馮:他在科達,管營銷。以前我們就是銷售經理,賣貨而已。他是學經濟的,把營銷、策劃帶來了,實際上陶瓷行業的經銷商制是邊程搞起來的。
劉:他在鉆石也分管過銷售,聽陳雄飛講。鉆石其實是最早把業務科變成銷售部的人,而且當時已經有了區域經理,整個市場按區域劃分。據說這在當時的業界是空前的。
馮:這一點邊程做了很大貢獻。他過來了,我們準備做,把李志林找過來。李志林是建國廠的,去過二廠當廠長,過來三水范湖管廠。作為陶瓷機械廠,我們設備賣給人家,人家不讓我們帶客戶去參觀設備,畢竟他們是競爭對手。那我們的客戶怎么辦?所以要做試驗工廠,這是一個出發點。在這之前,我們也嘗試了,尾款無法收回怎么辦?客戶給你磚坯。所以我們辦過拋光廠,拿磚坯加工后再賣掉。科達牌瓷磚——歐神諾陶瓷的前身,在花卉世界,我們在奔朗之前還搞過這么一個實驗工廠車間。后來買了范湖一間舊廠,實驗工廠就全部搬到那里了。
劉:做中示線吧?
馮:對。鮑工找李志林來做生產,邊程組織策劃,引入了營銷理念,里面有幾樣東西,經銷商制——把原來佛陶集團的代理、賒銷改成經銷,經銷與代理是完全不同的;把營銷策劃引入,包裝了歐神諾品牌的故事——海洋的故事、諾亞方舟的故事、橄欖枝,在石南大橋立了個廣告,“意大利經典,歐神諾陶瓷”。那個廣告一立就是好多年。
劉:當年這些故事都是邊程策劃出來的?
馮:是邊程和李志林他們一起策劃的,還有后來從佛陶過來的陳毅敏(后長期任歐神諾營銷老總)。
劉:我聽說當年科達做廣告,邊程有時候會親自跑到陶城報與廣告部人員一起搞策劃。
馮:他是學經濟的,有些理念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
劉:歐神諾當時在科達的框架下吧?
馮:開始是把歐神諾放在集團的框架下做的,后面發現有很大風險,就改變模式,于是歐神諾、奔朗等都改為自然人持股,誰經營誰占大頭,規避風險。
關于特地陶瓷
劉:現在我們談談特地陶瓷吧。你從2004年進入特地陶瓷,從營銷總經理做到董事長。特地陶瓷也從早期歐神諾系的副品牌獨立出來,并且定位也與歐神諾差不多了。但我總體感覺,特地陶瓷的發展速度其實是可以更快些的?為什么特地陶瓷不能擺脫現有生產體系的束縛,走出一條完全獨立的發展之路?
馮:我覺得這是一個公司頂層設計問題。特地陶瓷發展至今實際上也走出了自已的一條發展之路。
劉:我們知道你是一位很超脫的董事長,公司日常的事務盡量不插手。這其中,我們看到了盧勤管理科達機電的影子。你是如何考慮公司的治理結構的?盧勤或你的這種管理模式可以復制嗎?
馮:盧勤是老大哥了,我不能同比,但公司管理模式只能參考,不可完全復制。
劉:我們知道,鮑工和邊程的管理模式與盧勤就很不相同。你與盧勤采用了近似的管理模式,這是否是因為你們倆性格比較接近?
馮:不同管理者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可比!
劉:從科達機電到特地陶瓷,應該說,科達系或歐神諾系的創業元老們,都是行業中最早成功的一批“儒商”。但作為我們60后的這批成功的企業家,如何繼續保持事業上的激情?如何實現永續經營?這些問題你們現在考慮過嗎?比如說,接班人的問題,未來就是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這個你們是如何考慮的?
馮:對我來說還沒到考慮接班人問題時候,五十還沒到嘛,不過我認為這也是自然發展的過程。我不可能在第一線一輩子的,一定是交給有能力讓企業持續發展的人。
劉:據說盧勤從科達機電董事長位置退下之后,現在主要做些投資的事情。你對實業的興趣轉移了嗎?是否也在做些其他的投資?
馮:當前只考慮把特地做強做大!
劉:我記得2006年曾經跟你去過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參加“特地陶瓷綠墾基地”啟動儀式,這項植樹活動你們一直在堅持,很不容易。那片樹林長得怎么樣了?很大一片了吧?你現在每年都去嗎?好像經銷商都在參與?
馮:八年我只缺一年沒去,那地方樹不長個,此活動的精神在于調動更多的人去親自參與公益活動,持之以恒地參與。
劉:大家都知道你喜歡打高爾夫,打球、做董事長和做人之間有著什么樣的聯系?
馮:打高爾夫健康、陽光。其過程充滿智慧和自我桃戰 ,鍛煉身體,更磨煉意志,要打好并不容易,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會喜歡這一運動。打球的過程也是你性格、品性充分暴露的過程,所以也成為相互快速了解的商務環節。打球的成績不是重點,但打球的過程和做人、做事極其相關,球品見人品,歡迎約我打球!
劉:可惜我不會玩。謝謝你接受采訪!

人物簡介:
馮紅健,男,原籍廣東陽江,1966年出生。1984年考入華中工學院,所學專業為自動化(儀器儀表)。1988年大學畢業后自由分配來佛陶集團建陶廠。1995年離開建陶廠加盟科達,曾任科達郊邊廠(科達五金機械廠)廠長以及順德科達機械有限公司廠長、銷售部經理。2001年第30期清華大學MBA課程就讀。科達上市后,曾任科達機電第二屆監事會主席。2004年任特地銷售總經理,2006年任特地董事長。2007年至2009年,就讀中歐商學院(上海校區),獲EMBA(碩士)學位。現為廣東特地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長、佛山市陽江商會副會長。

 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頭條焦點
頭條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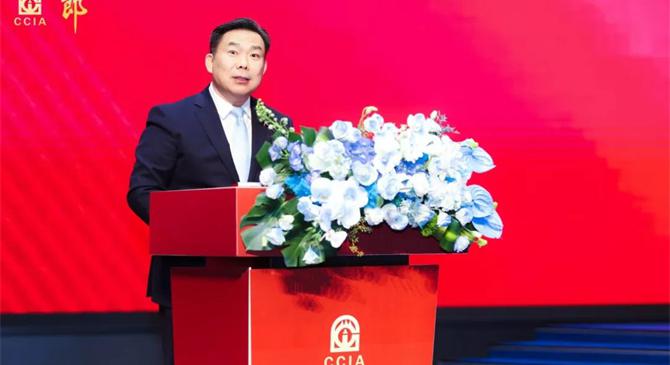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